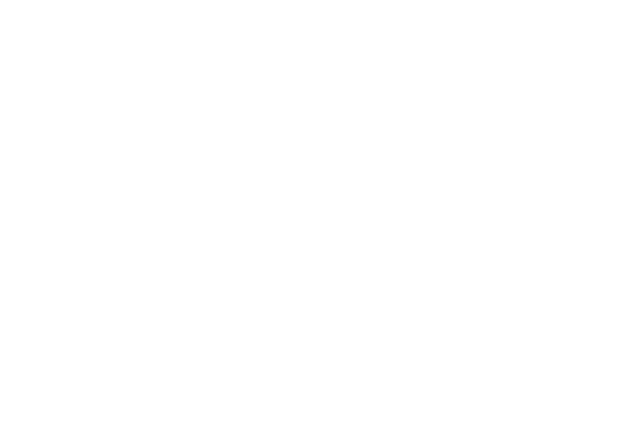
上海師范大學。上海發布(資料圖)
最高人民法院印發《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快建設智慧法院的意見》,指引法院管理信息系統的智能平臺建設工作。伴隨著這些文件的發布以及司法實踐的發展,我國司法工作開始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上海更是率先啟動“206”工程,打造未來法院人工智能系統。
司法領域應用人工智能的前景
實際上,碎片性的、尚未系統化的人工智能早已應用于司法工作。依照其最基本的含義——“使機器從事原本需要人類智能方可進行的工作”——案件檢索系統和案件信息管理系統便是典型體現,而法律法規電子資料庫更是成為全體法律人的必備產品。它們提高了司法工作效率、節約了司法資源,構成智慧法院建設的前期基礎。
只不過,在談及“人工智能”這一語詞的時候,絕大部分言說者和傾聽者都將其和“機器人技術”雜糅在一起,進而只將具有“擬人”行為的機器作為“人工智能”的載體。這一普遍存在的觀點,傾向于認為人工智能最終能夠做到一切人可以做的事情,因此,在司法工作中,機器人法官對人類法官的替代,便成為一種可以預期的未來。畢竟,機器人律師、機器人教師、機器人醫生都已經為人所熟知,而機器人法官所面臨的技術性難題必將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而消解。
人工智能自身的限度
“做人所能做之事”和“做人做之事”之間貌似微小的差異,卻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在前者的語境中,人工智能是輔助性的,而在后者的語境中,人工智能是替代性的,它的指向不是將人從勞動中解脫出來,而是將人從勞動中排斥出去,此時的人工智能雖然不被當作一個道德上的人,但在它做特定勞動的時候,它就“是”一個“人”。
如果僅從功能的角度來說,它們殊無二致,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運算速度遠高于人腦運算速度的情況下,只要算法本身不存在內在的漏洞,人工智能做某事的能力甚至會優于同等條件下人做此事的能力。可是,二者在意義層面截然不同。作為替代性的人工智能不需要考慮人的因素,因為它已經完全承擔了這一事項。因此,盡管人工智能未必和“意識”相關,甚至有極大的可能與“意識”毫無關聯,但人類是否能夠有意識地介入到“無意識智能”的領域,對于人類社會來說,意義截然相反。畢竟,在算法以及與其相關的計算能力不如人工智能的情況下,如果人的意識不能有效介入人工智能,那么,占主導地位的將是后者。
人工智能時代法官的自覺
歐美國家人工智能化起步較早,并且廣泛應用于司法領域。但美國埃里克·盧米斯(Eric Loomis)案的進程表明,作為司法工作核心的法官,并沒有清晰地認識到“做人所能做之事”和“做人做之事”之間的差異。盧米斯因偷竊槍擊者拋棄的汽車而被警察誤當作槍擊者予以逮捕,鑒于其存在偷盜和拒捕行為,此案進入訴訟程序。基于人工智能“COMPAS”的測試,盧米斯的再犯風險極高,據此,法官裁決他服刑6年。盧米斯提起上訴,但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支持了下級法院的裁決,并肯定了其裁定理由:人工智能“COMPAS”的風險評估是借助獨立的子項和復雜的算法完成的,最終從1到10的級別評定具有中立性和客觀性。
在這一案件中,無論是初審法官,還是州最高法院的法官,都選擇了這樣一種推理路徑:人工智能是無感情的,因此它是中立而客觀的,進而它評測的結果就是中立而客觀的,值得采納。在這一措辭中,法官在兩種“想象”中搖擺:一方面,人工智能是為法官所用的,它是一種輔助性工具,因此它的結論不需要經受相對人的質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作為“專家證人”的替代者存在的,它的算法比之人工詢問更加具有可信度,于是它的結論是決定性的證據。這導致原本法官需要針對盧米斯的個案情形進行具體的判斷,但他們實際上采納了人工智能的判斷卻又想不承認這一點。
美國這一案例展示了一個圖景:居于判斷之位的法官盡管形式上行使了判斷的權力,但實際上并沒有運用判斷的權利。他們沒有體現出創造新知識的智識,而選擇順從于人工智能的判斷。當其他人質疑這一判斷時,借助人工智能的重疊想象,法官將判斷的責任歸之于人工智能,并通過責任轉稼的方式將自身保護起來。
誠如阿倫特所言:“我們關于是非的決定將依賴于我們對同伴的選擇。”盡管這些法官是有思想的,但這一思想僅僅歸于活動的序列,而無法歸于行動之列。只有他們自己意識到他們自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判斷,但這一意識無法構成通感,因為觀察他們行為的其他人認為這一判斷的行動來自于人工智能,而他們實際上也樂于接受其他人的這一判斷。當美國的法官作出這一選擇之時,他們拒絕通過判斷力將自己與當事人(即其他的人)聯系起來,既否認了判斷力這種屬于人類的能力,同時也就否認了法律賦予法官的重要權力。
因此,人工智能時代法官要有自覺意識,即人工智能的作用是作為判斷的輔助。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法官確實是絕無可能的,因為,判斷的權力將始終把握在法官的手中。












 徐匯校區:上海市徐匯區桂林路100號
徐匯校區:上海市徐匯區桂林路10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