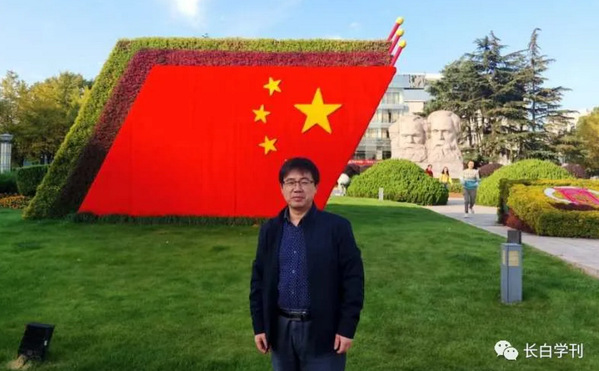
作者簡介:耿步健,男,中共黨員,法學博士,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師范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研究員,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教學與相關理論研究;兼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專家,教育部學位中心評審專家,江蘇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區域科學協會生態文明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其他部省級課題7項、主持校級課題近10項,在權威報刊發表論文60余篇;出版專著2部、教材2部,參著4部。曾獲省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進個人、省級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等。
摘要:新春伊始,全國上下都在進行著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戰”“總體戰”“阻擊戰”,這場戰“疫”無疑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驗。這次重大疫情從某種意義上也說明了當前我國生態環境治理和重大疫情防控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漏洞和弱項,需要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角進行反思。“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為實現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態環境治理科學化提供了新視野。要做好重大疫情防控,需要與生態環境治理有機結合,并按照“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樹立科學的生態環境治理觀,更好地指導能夠有效防控重大疫情的生態環境治理實踐。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習近平生命共同體思想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研究”(18BKS027)。
正文
當前,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正在進行著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戰”“總體戰”“阻擊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暴露了我國生態環境治理和重大疫情防控方面存在的問題,需要我們從我國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的視角進行認真的反思,并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樹立科學的生態環境治理觀。當然,如何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樹立科學的生態環境治理觀,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筆者認為,必須“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1]。具體地說:補野生動物保護之短板,堵生態環境治理制度體系之漏洞,強重大疫情防控之弱項。
一、“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為實現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態環境治理科學化提供了新視野
對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原因,許多學者從引發重大疫情的病毒來源和防控的速度、力度、適度等方面去研究,很少從生態環境治理觀的視角去進行反思,沒有把生態環境保護與野生動物保護聯系起來,沒有把人與動物(包括野生動物)的關系納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之中。這就造成了在現實的生態環境治理中,把人與動物的關系排除在生態環境保護的制度體系和執行機制之外,因而也就不可能從正確而又理性地處理好人與動物(特別是野生動物)和諧共生的角度,去全面思考重大疫情發生的各種原因及如何更為有效地避免重大疫情的再次發生。習近平在2020年2月14日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再次強調:“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1]如何做好這次疫情給出的而又能令人民滿意的考卷,值得我們跳出既有思維模式去進行辯證而又創新的思維。這次重大疫情說明,有必要從“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視角,把人與動物的關系納入生態環境治理范疇,樹立科學的生態環境治理觀。
(一)“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的基本內涵
“生命間性”這一概念緣起于地球所有生命所組成的共同體(即“生命共同體”)。關于“生命間性”的研究起步比較晚,研究的學者比較少,一開始主要從生命哲學的意義視角進行理解和研究,認為:生命間性“是指人類生命具有的不僅把自己思為生態的三重生命而且還用生命的理念看待、對待其他生命的一種生命特征”[2]68。這其中所說的“三重生命”是指生物性生命、社會性生命、精神性生命。但僅從生命哲學的視角理解“生命間性”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在眾多的生命類別中,人的生命是最智慧的,能夠主宰大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但其他生命只具有生物性生命,不具有社會性生命和精神性生命,不能主宰人類,因而需要從更廣泛的生態意義上去理解和把握“生命間性”。也就是說,“生命間性”的概念更符合生態哲學發展的要求,是一種重要的生態哲學觀,能夠讓我們更好地思考人與自然生命物種的邊界及其和諧共生的關系,從而為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和有效防控人類重大疫情提供生態哲學觀基礎。從生態哲學意義上說,“生命間性”是指人與大自然的其他生命體之間既緊密聯系而又具有各自的生命特性、需要人類對其他生命予以尊重的一種生態哲學觀。“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強調“覺醒的生態意識”[3]95,要求人們要敬畏生命、尊重大自然各類生命體的生命權利和生存秩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還特別強調要“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1]。加強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首要的是要樹立“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把生態環境治理與重大疫情防控緊密地結合起來。
(二)“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是對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生態哲學觀的傳承和對西方“人類中心主義”哲學觀的反思
“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有其演化和發展的過程。中國古代生態哲學觀強調“天人合一”,要求人們“道法自然”,緣于生產力低下和愚昧無知而對自然作出的膜拜和順從,總體上屬于后人所提出的“自然中心主義”,強調人應該在尊重和順應自然的基礎上與包括其它生命體在內的大自然達成和諧與統一。在“天人合一”生態哲學觀主導的社會里,動物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護,不同生命體之間的主體性及主體間性得到了自在自發自為的呈現。如《孟子》里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論語》中也有“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甚至我國佛教一直強調不殺生。而在西方社會,一直盛行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觀,這種哲學觀把滿足人的需要作為目的,把除人之外的大自然作為手段,因而本質上屬于以征服、掠奪大自然為目的的反生態的哲學觀。西方社會很早就相信“大自然是為了人的緣故而創造了所有的動物”[4]。對于這一點,可以從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得到證明:“經過馴養的動物,不僅供人口腹,還可供人使用;野生動物雖非全部,也多數可餐,而且[它們的皮毛]可以制作人們的衣履,[骨角]可以制作人們的工具,它們有助于人類的生活和安適實在不少。如果說‘自然所作所為既不殘缺,亦無虛廢’,那么天生一切動物應該都可以供人類的服用。”[5]23這一哲學觀到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為資本家野蠻掠奪自然、追逐高額利潤、造成嚴重生態危機的同時,也造就了資產階級貪婪揮霍、荒淫無度的糜爛生活。也正因為人類對自然的不尊重、對自然的野蠻掠奪和揮霍,導致了西方社會曾經非常嚴重的生態危機,并造成了諸多導致無數人和牲畜死亡的生態環境公害事件,其中也有一些因為生態環境糟糕和退化而導致的各種傳染病毒疫情,如14-17世紀發生于歐洲的多次傳染病毒疫情都與生態環境的惡化有關。為此,恩格斯專門告誡人們:“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6]313
(三)“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是對西方包括動物保護主義者在內的生態哲學觀的辯證借鑒
隨著西方生態危機日益嚴重,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觀,并從生態環境保護的層面思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形成了“動物保護主義”“生物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等的生態哲學觀。其中,“動物保護主義”是與本文主題直接關聯的,因為導致人類重大疫情的病毒,原本與我們人類無關聯,但由于不注重動物保護特別是野生動物保護,造成了寄宿于它們身上的病毒有機會感染人類并造成人類社會可怕的瘟疫。當然,動物保護主義者在最初提出“動物保護”這一理念時,主要還是基于部分動物(比如狗)對人類有某種感知能力甚至有某種親密、依賴和忠誠的情感,要求人們必須尊重它們對自身生命的渴望和權利。也有一些動物保護主義者認識到大自然存在一條生物鏈,對于瀕危或趨于滅絕的野生動物必須予以保護,以保證生態的平衡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當然還有少數激進的動物保護主義者將動物保護泛化到所有動物上,這就走了極端。因為,野生動物是否需要保護,要看某種野生動物的數量是否有利于生態平衡和人居生態環境的安全。總之,雖然“動物保護主義”的相關觀點并不完全屬于生態哲學,有些屬于生命哲學,但從他們的相關觀點中,我們感受到了人與其他動物之間存在著生命間性。申言之,要有效防控重大疫情,必須樹立以“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為指導的科學的生態環境治理觀。
二、“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對于樹立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科學生態環境治理觀的基本要求
按照“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要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樹立科學的生態環境治理觀,思考不同種類生命體之間的倫理關系和倫理秩序,創新思維觀念,努力建設一個和諧安全有序的大自然生命共同體。
(一)充分認識各類生命體都有其獨特的生存空間和適應能力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就屬于“生命共同體”的大自然來說,各個生命體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間和適應能力,相互之間既矛盾、斗爭,又和諧、統一。正如恩格斯所說:“自然界中無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諧也有沖突;有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則既有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合作,也有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斗爭。”[6]300和諧、合作也好,沖突、斗爭也好,都是為了取得生存繁衍的空間并努力適應那里的環境。事實上,每類生命體在獲取食物過程中(或無意與被動之中)感染上新的細菌或病毒的最初,都會出現生病、死亡,但在長期的生存與繁衍中,這些生命體也在進化,特別是自身的免疫系統也會不斷進化出能夠有效應對這些細菌和病毒的辦法,以保證即便身體感染上這些細菌和病毒,也能與它們相安無事、和諧共生,這也就是達爾文所說的生物進化中的“自然選擇”。比如狗身上的狂犬病毒、黑猩猩身上艾滋病毒等。造成人類歷史上多次瘟疫的病毒,經證實大多來自野生動物體內所攜帶的病毒,比如蝙蝠、果子貍、竹鼠、獾,等等。據美國某雜志刊載的相關研究表明:“新出現的人類傳染病中,有60%以上源自動物,這些人畜共患病的動物源性疾病中又有70%以上來自野生動物。”[7]為什么人類每一次發現的“新型病毒”都會“鐘情”于野生動物,原因就在于這些野生動物在長期的生存繁衍中產生了抗體,對寄生于它們身體的病毒具有超強的免疫力。既然這些野生動物和寄生于它們體內的病毒相安無事、和諧共生,那這些野生動物也就成了它們體內寄居的病毒的自然宿主。
(二)充分尊重寄宿病毒生命體的環境邊界并保持安全距離
基于“生命間性”的生態哲學觀,如果人與這些成為寄宿病毒生命體的野生動物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并進行有效的防控,那人類感染上野生動物體內病毒的機率就會小得多(至少不會是主動受感染和傳播),野生動物體內的病毒也就不可能造成人類那么多形形色色恐怖的瘟疫。過去,由于自然科學的不發達,對于自然界眾多的細菌、病毒等傳播病癥沒有很好的防疫措施,人類被傳播感染上致命細菌或病毒從而導致可怕瘟疫的情況還是時有發生的,一旦被感染上就只能等待死神的降臨。所以在疫情來臨時,如果不想讓其他人和其他地區的人感染,最好的方式就是自我阻斷與外界的交往,直到“瘟神”自我滅亡或隱去。這一點可以從歐洲十七世紀中期發生的“黑死病”這一烈性傳染病的防控中得到驗證。這場瘟疫導致當時歐洲的人口減少一半,但令人奇怪的是英倫半島的中北部沒有任何人被傳染,后來人們發現這是因為英倫半島南北接壤處一個叫亞姆村的村民,本著“即便是死,也要善良”的精神信仰,沒有逃離,并自覺筑起通往英倫半島中北部出口的一道石墻,以免外人進村被感染和傳播。基于“生命間性”的生態哲學觀,人在防治傳染性疾病的過程中,開始注意到了人居環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并加強對寄宿有傳染性細菌和病毒的源頭的預防,不自覺地體現出來了令后人反思和總結出的“生命間性”的生態哲學觀,它幫助我們更好地思考不同生命體的生活習性和結構特征,幫助我們更好建立起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特別是野生動物保護意識。從傳染病的防控角度看,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研究如何更好地科學防范野生動物身上的細菌或病毒傳染給人類的方式、方法。此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無疑與人們對于“生命間性”的無知與無畏的不良生產、生活習慣有關。
(三)充分把握寄宿于野生動物生命體的各類病毒特點及傳播路徑
從科學角度來說,寄生于野生動物生命體給人類造成致命危險的病毒都有其宿主、存活溫度、傳染與潛伏期規律(傳播對象規律、傳播方式規律、潛伏發作規律,等等),如果我們把握了這些,就能夠大大減少感染有傳播特點的致命病毒并繼而導致瘟疫的風險;否則,被這些致命病毒感染并傳染給他人繼而導致瘟疫的風險就會大大增加。如,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盡管到現在不知道其真實“身份”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其真正的宿主是誰(盡管有證據證明可能是猴子及猩猩等野生非人靈長類動物),但人類目前對其總體特征已掌握:屬于人畜共通病毒;存活的溫度是“在血液樣本或病尸中可存活數周;4℃條件下存放5周其感染性保持不變,8周滴度降至50%,-70℃條件可長期保存”[8]1531,1539,傳播方式主要是飛沫傳播與病毒源的直接接觸,如與寄宿有該病毒的野生動物(包括尸體)、感染該病毒的患者體液、皮膚、黏膜等的直接接觸。再比如,2002年末發生的“非典”(SARS),盡管最終是被控制住了,但是SARS病毒卻沒有從根本上消滅,經過多年的研究,才真正搞清楚SARS的宿主原來是“菊頭蝠”(又稱“中華菊頭蝠”)[9]465,果子貍是因為經常捕食菊頭蝠才感染上SARS病毒,人類因為食用果子貍而導致SARS病毒又被傳染到人身上。患者又通過直接接觸(人與人)、間接接觸(如共用電梯、樓梯)等方式傳染給其他人。SARS病毒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可以通過患者的排泄物傳播[10]633,一旦排泄物中的病毒通過某種途徑揮發到空氣中,那后果也是不堪設想的。但也有些病毒,不具有人畜共通性,如豬瘟病毒,因而對人沒有影響[11]13。
三、按照“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不斷推進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態環境治理科學化
按照前文所述,目前我國生態環境治理存在一個大的漏洞,即沒有把野生動物的保護納入生態環境保護的整體系統中,致使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及相關的法律沒有與野生動物保護法有效銜接,使得野生動物保護沒有上升到生命共同體意識的高度而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沒有將生態環境治理與重大疫情防控有機聯系起來,去認真審視人與動物(包括野生動物)如何科學無害地接觸相處,才能保證生物安全繼而更好地確保人類安全。
(一)建立和完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態環境治理制度體系
雖然每次重大疫情防控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和統籌安排、各級社會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和配合下一定能取得最后的勝利,但代價實在太大。這就要求必須把推進國家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與常態化的重大疫情防控結合起來,按照“生命間性”的生態哲學觀,不斷建立和完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態環境治理制度體系。首先,認真制定和完善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法規。要通過制度性安排加大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懲罰力度,讓野生動物的生命得到尊重和維護,讓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的違法犯罪分子付出沉重的代價。當年的“非典”就是因為人類沒有嚴格遵循野生動物保護法。其次,要進一步完善與野生動物保護法相銜接的生態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野生動物棲息地(生存空間)的生態紅線保護。規定人居生活用地、畜牧業用地與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合理邊界與間隔,防止野生動物有機會進入人居生活用地及畜牧業用地,或被這些野生動物咬過并感染病毒的中介被人工飼養的動物接觸或誤食,從而導致病毒的傳染。上世紀90年代末馬來西亞發生的嚴重危害家畜、家禽和人類的尼帕病毒,原因就在于我們人類對野生動物領地的“侵占”,把養豬場建到了蝙蝠棲息地的旁邊,結果一個被蝙蝠吃剩的感染有蝙蝠體內病毒的水果掉到了豬圈,豬吃了就被感染了,豬又把病毒傳染到了人。再次,進一步完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人居環境建設的相關制度。如要通過制度規定房屋結構一定要按照能通風、采光好的標準設計,禁止建“墓室式”的建筑,必須保證道路、花園及周邊環境的清潔美麗,必須保證下水安全通暢,必須對人居環境定期進行防疫消毒,等等,徹底杜絕病毒傳播感染的可能。
(二)建立和完善社會重大疫情防控的“共棲”型生態環境治理模式
“共棲”(COHAB)型治理模式是由德國科學家格哈德·克尼斯(Gerhard Knies)提出,其本意是為應對包括生態問題在內的全球性挑戰、保護和發展全球公共利益而提出的一種國家之間進行合作的全球治理模式。它意味著“國家和其他地理單位將自愿組織在一起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互相對抗或漠視”[12]241。盡管這一理念作為全球治理的一種模式過于理想,但對于當前和今后的重大疫情防控有著非常好的借鑒意義。首先,按照“生命間性”的生態哲學觀,大自然的每個生命體的命運都是緊密相連的,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在保護野生動物的同時,也應該借助于互聯網媒體技術的發展,建立全球非官方的野生動物保護的“共棲”治理模式。要共同建立野生動物保護的信息資源網,引導全球的野生動物保護朝著安全、健康、文明、有序、共贏的方向發展,特別要在野生動物的生活習性、可能的寄宿病毒等方面進行常態化的跟蹤研究和信息共享,搞清楚不同野生動物生命體寄宿的病毒特性、發病機理與傳染特點,以及對這些病毒如何進行有效防控等。其次,要建立由政府推動的全球范圍內的野生動物病毒防控的合作機制,定期進行野生動物保護工作人員的交流培訓,提高他們在阻隔和防控來自野生動物病毒的實戰能力和水平,并通過他們向全社會進行野生動物保護及野生動物病毒防控方面的相關知識,保證整個社會對于野生動物保護及野生動物病毒防控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不再因無知無畏和不注意衛生安全的生產生活方式導致來自野生動物病毒疫情的發生。再次,“共棲”治理模式不能僅限于野生動物保護和來自它們體內傳染病毒的防控,必須將“共棲”模式擴大到生態環境保護,將野生動物保護和來自它們體內傳染病毒的防控,納入整個生態環境的系統化治理格式之中,爭取各國政府和相關國際組織的支持和幫助。
(三)建立和完善常態化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態環境治理運行機制
重大疫情能否有效防控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一個國家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驗。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13]。由新型病毒引發的重大疫情有其偶然性,但任何偶然性都是孕育在必然性之中的。在“非典”疫情發生后,我們并沒有深化這種反思和警醒;相關政府部門在重大疫情聯防聯治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方面還非常滯后;相關研究還停留在已有的資料上,特別是各種疫情病例大多數來自比較滯后的媒體報道,如“非典”疫情發生了才去研究SARS病毒等,大多數搞流行病研究的人員沒有就可能出現的新型病毒深入疫區或者野生動物保護區進行研究;大多數醫院找不到訓練有素、基本功扎實的醫護小組,受二次傳染的醫護人數不在少數;一些機構在疫情來臨時,隱瞞隱藏甚至簡單應付,喪失公共信任資本;個別但又特別關鍵的病毒疫情科研人員喪失職業道德底線,等等。這些無形當中都構成了潛在的風險。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資本主義制度不可比擬的顯著優勢,在疫情來臨時黨和政府的動員力、組織力、執行力都不容懷疑,能夠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地抗擊疫情,但疫情還是不來的好。所以必須建立和完善常態化的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態環境治理運行機制:第一,加強新型病毒的研究和知識宣傳,加強相關防治人員的專業培訓,強化普通百姓的重大疫情的防控意識;第二,梳理、排查引發重大疫情的新型病毒傳染風險點及相關對策措施,建立重大疫情的信息公開機制,補齊公共生活生態環境治理的短板;第三,加強市場監管,“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14],徹底斬斷新型病毒的傳播感染路徑。另外,在建立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生態環境治理運行機制方面,我們既要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也要學習借鑒國外的科學做法,更重要的是把“生命間性”生態哲學觀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每一個環節細微處。
參考文獻:
[1]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N].光明日報,2020-02-15(1).
[2]操奇.底線生命倫理證成的可能性:生命間性論[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4).
[3]李培超.自然的倫理尊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楊通進.環境倫理:全球話語,中國視野[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5][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6]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倪浩,范凌志,任重.野生動物為何易成病毒傳染源[N].環球時報,2020-01-23(13).
[8]Piercy TJ, Smither SJ, Steward JA, et al.The Survival of Filoviruses in Liquids, on Solid Substrates and in a Dynamic Aerosol[J]. J Appl Microbiol, 2010, 109(5).
[9]佚名.科學家進一步證實SARS病毒來源于中華菊頭蝠[N].中國醫藥生物技術,2013(6).
[10]李敬云,等.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排泄物中SARS病毒生存和抵抗能力的研究[N].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3(7).
[11]農業農村部.非洲豬瘟不是人畜共患病不會感染人[N].畜牧業環境,2018(1).
[12][德]魏伯樂,[瑞典]安德斯·維杰克曼.翻轉極限:生態文明的覺醒之路[M].程一恒,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8.
[13]佚名.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強調: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光明日報,2020-02-06(1).
[14]佚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加強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N].光明日報,2020-02-04(1).
原文載于《長白學刊》2020年第2期1-6頁。
責任編輯:鄭偉
鏈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czMzgwNQ==&mid=2651354105&idx=1&sn=124f5b3e71515e72cffd12bdd6f078f0&chksm=80f4397bb783b06dce8e174aa63b0bbb04215c8bef02470851f74b4526ad52eea638e50a2633&mpshare=1&scene=1&srcid=0306mhefcwqQDKLhrtvZ9T19&sharer_sharetime=1583488660457&sharer_shareid=efe1fe33906b357899bfb3509eccfd21#rd












 徐匯校區:上海市徐匯區桂林路100號
徐匯校區:上海市徐匯區桂林路100號